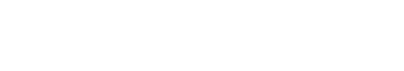党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社区矫正制度”,四中全会提出“制定社区矫正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要第一次审议《社区矫正法》,由于对“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在顶层设计失误”的问题尚未引起高层关注,这将会直接影响立法质量。
执法机构设置是我国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和基本保障,建议将社区矫正执法工作与司法所脱离,在县(区)级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隶属于省级罪犯管理机构或公安机关,确保社区矫正在维护社会稳定、预防减少犯罪、保障公民权利、降低刑罚成本、执法公平公正、巩固执政党执政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一、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有违中央关于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
社区矫正是将法院的刑事裁决在社区加以实现的刑罚执行活动,执法公正是司法公正的延续和实现。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对执法机构设置的指导原则是:有利于法治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省级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执法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相对集中执法权,着力解决权责交叉、多头执法问题,建立责权统一、权威高效的执法体制,减少执法层级。
我国的司法所是县级司法局和乡镇、街道政府双重管理下的法律服务机构,现实的在编人员为1~3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乡镇、街道政府中设立司法助理员的基础上演变而成。司法所在我国社区矫正试点之前没有刑事执法的性质和功能,主要承担人民调解、法制宣传等八项任务。2012年“两院两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并生效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首次将司法所明确为执法主体。2013年司法部起草的《社区矫正法》建议案第八条作出了同样的规定。
但我国社区矫正从2003年试点至今的实践证明:司法所管理社区矫正不利于执法队伍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全国检察机关在2015年集中部署开展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专项检察活动,发现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虚管问题日益凸显。如果不断发生脱管、漏管和虚管现象,使我国刑罚执行的权威性、严肃性及司法的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也是给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提供了机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重大的隐患。
研究表明:司法所难以胜任社区矫正工作。司法所在人、财、物和时间精力方面均难以保障对社区矫正的专业化管理,司法所受县级司法局、乡镇、街道政府、政法委、社团组织多头管理,责权不清、相互扯皮、效率不高,司法所管辖与基层行政区划完全吻合,存在地方权力干预执法问题。这种运作模式如果继续下去,难以保证社区矫正服务法治建设的目标。
二、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削弱了社区刑罚执行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我国在2003年六省市率先开展社区矫正试点之前,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是由公安派出所承担。公安管理的优势是有利于体现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缺点是将这项工作放在派出所兼管不利于专业化的发展。
英国在2007年之前的一百年间一直由公安机关(内政部)管理社区服刑人员,在与行政区划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内设置缓刑办公室,工作人员在10~40人的范围内不等,按工作人员与社区服刑人员的比例设编。目前,加拿大联邦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是归联邦公共安全部管理。
我国社区矫正试点采取将该项工作由公安派出所转交司法所,不仅没有加强专业化管理,而且将执法工作交由非执法性质的机构来承担,大大削弱了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公安机关有明确的执法权力,有丰富的犯罪控制的资源,必要的强制措施和快速的反应能力,而司法所相差甚远。
三、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拉大了与各国在执法机构设置方面的差距
各国的基层社区执法机构设置在形式上并非相同,但共同遵循了三项基本规则:
一是归属于国家的强力机关。强力机关是指国家法律赋予的具有执法或司法权的机构。除有的国家归属于公安机关外,在德国、美国联邦和美国一部分州归属于法院,作为司法分支机构,专门从事缓刑管理。由于法院负责判处缓刑和缓刑收监,有利于司法与执法的沟通,提高审前调查质量、对缓刑执行信息的及时反馈和对缓刑违规的及时收监。我国台湾地区相类似的机构是观护人室,归属于地区法院检察署;而更多国家的机构设置是归属于专门的罪犯管理机构,英国2007年在法务部下设罪犯管理局,美国大部分州政府下设惩教局,承担对监狱和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法律赋予对服刑人员可行使警戒具和拘留的刑罚执行权。
二是专职而非兼职。社区执法基层机构以团队形式运作,工作人员有细化分工,有利于提高效率。
三是摆脱行政的干预。绝大多数国家的机构采取国家或省(州)级人财物统一管理,尽可能减少地方干预,保障执法公平公正。
我国司法所管理社区矫正完全违背了以上规则,司法所的上层领导机构(县级司法局或乡镇街道政府)均不是法定的国家强力机构;司法所是兼职而非专职管理;司法所归属于乡镇街道政府,人际关系的地方化和复杂性,会直接影响执法的公正。
四、司法所作为社区矫正执法主体不利于提高工作效率
非专业化的管理严重影响了工作效率。由于社区矫正工作岗位责任大、风险大、工资待遇不高。司法所人员大多不愿从事这项工作,造成流动性大、更换频繁,影响了工作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少地区人员编制不能满足,聘用低工资的合同制人员,他们多把该岗位作为过渡的平台。普遍的工作状态是:忙于应付一些表面化工作,缺乏针对性的严格管理和教育矫正。
由于多头管理、非专业化、职责不清、造成工作效率低下。据统计,上海市共有司法所专职从事社区矫正的公务员276人,选派218名戒毒人民警察,社区矫正社工635名,专职工作人员共1129名,社区服刑人员8515名(2015年),人均管理7.54个社区服刑人员。北京市共抽调406名监狱、戒毒干警从事社区矫正,全市326个司法所每所至少一人专管社区矫正,另外,还招聘了751名社区矫正社工或协管员,共有专职工作人员1483名,现有服刑人员4000名(2016年),人均管理2.7个社区服刑人员。不犯社工和协管员的话,人均管理5.46个社区服刑人员。而英国一名工作人员平均管理35名罪犯,美国一名工作人员平均管理70名罪犯,我国台湾地区一名工作人员平均管理150人。我国司法所管理社区矫正的低效率,违反了开展社区矫正降低刑罚成本的初衷。
五、对我国社区矫正执法主体设计的建议方案
建议将社区矫正执法工作与司法所脱离,在县(区)级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隶属于省级罪犯管理机构或公安机关,省级罪犯管理机构是指将现有省级监狱局更名,工作范围扩大到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实行省级人财物的统一管理。对罪犯管理实行统一经费预算,在罪犯人数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社区服刑人员管理的经费,势必要按比例减少监狱管理经费。执法人员一方面从司法所包括公安、监狱和戒毒机关抽调能够胜任工作的人员,另一方面按照准入标准从社会招聘。隶属省级罪犯管理机构的好处是有利于将监狱和社区罪犯管理的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不足是社区罪犯管理机构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而归属于公安机关的好处是有利于增强执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有利于充分借助公关机关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丰富资源,而且公安也有长期管理社区服刑人员的基础。可在省级公安机关下设社区罪犯管理局(总队),待社区矫正机构运作步入正轨、条件成熟后整建制移交省级罪犯管理机构。建议方案需经过充分论证,经立法机关授权先行先试,对方案进行跟踪评估,待成熟后经国家立法在全国实施。
清朝末年,我国刑罚制度的残酷和野蛮,受到西方列强的批评和谴责,促成我国清末出台了《大清新刑律》和《监狱法》,使我国刑罚制度在现代文明的道路上迈出了大步。一个世纪过去了,发达国家刑罚制度已进入“以社区刑罚为中心”的新时代,而我国却仍奉守“以监禁刑为主、以社区刑为辅”的过时模式。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试行旨在使刑罚制度的改革步入现代化轨道,对社会的稳定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社区矫正机构设置的失误大大影响了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进程。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需要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在党中央和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下,尽快形成科学的社区刑罚执行机构设置的改革方案,加快改革的进程。
浙江省台州市于2014年已进行社区矫正工作与司法所分离的尝试,效果很好, 安徽省蚌埠市拟进行这种分离的尝试,许多省市自治区实务部门已感觉到司法所不适合承担社区矫正的管理,但有碍于“两院两部”的文件规定,不敢轻举妄动,希望决策部门尽快采取措施。